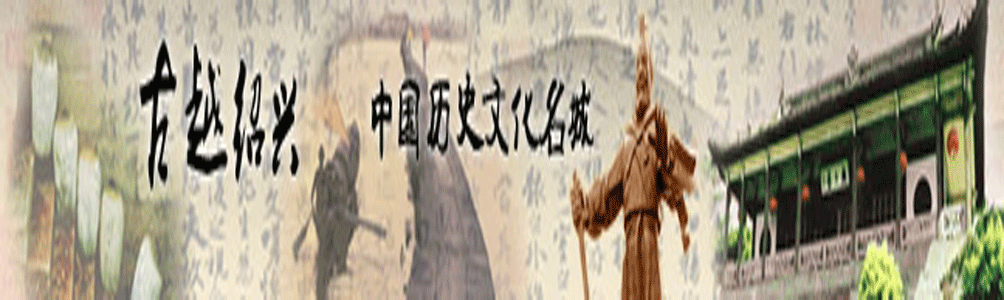在我院俞志慧教授的指导下,由我院三个学生科研项目《古文观止》的编辑与传播、绍兴古桥的历史与文化、《越郡风俗词》研究组成了绍兴记忆研究团队。年10月10日,《绍兴晚报》越文化专栏刊登了我院学生陈微的《倾听越郡风俗词中的“采桑曲”》。陈微同学所负责的“《越郡风俗词》研究”课题,现已申报年绍兴市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附原文:
绍兴桑蚕业的历史和《越郡风俗词》中的采桑曲
人文学院陈微()
众所周知,绍兴不仅是水乡酒乡桥乡,还是一个著名的纺织原料产地。柯桥轻纺城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轻纺专业市场。但是,各位可能有所不知,绍兴地区的纺织品起步,曾经是远远落后于国家平均水平的。
蚕桑丝织技术是中国的伟大发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就开始养蚕。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桑、蚕、丝、帛等字形。《尚书·禹贡》中有“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说的是洪水退去以后,人们从山丘上下来,到平旷地带采桑养蚕。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蚕丝织业迅速发展,丝织技术也不断进步。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一段话,说的是晋公子重耳流亡时,到了齐国,齐桓公把女儿姜氏嫁给他,他安于齐国的生活,但随从打算离开,就在桑树下谋划,采桑养蚕的女奴听到此事,就告诉了姜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养蚕是一项工作,专门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员,就是“蚕妾”。
那时的绍兴却还没有这个产业,庄子《逍遥游》中说:“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有个商丘一带的商人,带了一批华丽的纺织品到越国去销售,但越人剪断长发,身刺花纹,帽子衣物对他们毫无用处。《史记·赵世家》唐张守节《正义》记越人文身之法“刻其肌,以青丹涅之。”这个故事体现的是当时的越地风俗,人们都剪掉头发,在身上画出图案,关于这点,东汉时期的学者应劭认为,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这是古代越人“习水”而避蛟龙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既然越人不穿衣服,说明当时绍兴是没有纺织原料的。
那么,绍兴地区最早的纺织原料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要说到吴越争霸时的范蠡大夫,是他引进了擅长种葛的齐(今山东一带)人,在葛山(现绍兴市委党校附近)种葛,《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记载:“葛山者,勾践罢吴,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于吴王夫差。去县七里。”讲的是越王勾践兵败后退于会稽山,听从范蠡的建议在葛山上种葛,让女工织成布献给吴王夫差。《越郡风俗词》也有诗云:“种葛山头芊蔓滋,君王尝胆几多时。当年功业不长在,空有妇人作苦诗。”可见,“葛”是绍兴出现的最早的纺织原料。当时还有一种纺织原料,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西施浣的那个“纱”。一般认为,“纱”就是苎麻,本地人称为“苎萝”,为荨麻科麻植物,多年生草本,茎部柔韧而有光泽,取其茎皮(纤维)用来织布、结网。
与吴越争霸差不多时间,有一个因争桑引发的战争的故事。《吕氏春秋·察微》载:“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於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的卑梁之衅,两地女孩争夺桑叶导致了吴楚几十年大战,引人唏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乱对黄河流域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隋朝时中国桑蚕业的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到了唐朝,越地桑蚕业开始真正发展起来,这得益于一个叫薛兼训的军官,《唐国史补》里这样说道:“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娶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矣。”不得不说,薛兼训这个人实在是聪明,他出台优惠政策,让手下未婚的士兵去把北方擅长养蚕制丝的女孩娶来,这样的巧手媳妇,一年就娶了数百个,然后就大大促进了越地桑蚕丝织产业的发展,贞元(年~年)以后,越州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达数十种之多,因而那时有“辇越而衣,漕吴而食”的说法,也就是说天下的衣食要从吴越一带车载船运方能维持。五代十国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又一次遭受战争的破坏,而建立在两浙的吴越国,对本地区的蚕丝开发却十分重视。吴越王钱镠在《钱氏家训·八》中说:“吴越境内,绫绢绸绵,皆余教人广种桑麻。”而到了宋朝,《宋会要辑稿·食货》中则记载了北宋中期各地汇集到朝廷的丝绸总数,长江下游东南地区平均每年北运的布帛达多万匹,几乎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而东南各路中,负担最重的是两浙,据年的上供记载就已达98万匹。不仅数量大,丝织品的种类也是很多,当时越地尤以越州寺绫出名。编定于宋神宗熙宁五年()的《会稽掇英总集》卷二十中这样描写当时越州的丝绸生产:“俗务农桑,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
再后来,绍兴养蚕制丝行业渗透到了绍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留下了十分有趣的记载,譬如《越郡风俗词》所保留的《田家采桑曲》三十首就有一百多年前绍兴地区关于桑蚕丝织产业的描写,和严肃的历史记录不同的是,它们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种桑养蚕既是谋生之道,也是日常乐趣。
当时养蚕规模应该是比较大的。从第一首“邨南舍北又墙东,嫩绿纷披扇晓风”,第二首“傍隄栽遍荫参差”还有后面诗歌中反复出现的“绿云”、“绿荫”、“密阴”、“桑荫”等词中可见一斑。现在的绍兴越城区已少见大片的桑树林,但上虞有一个被誉为“江南蚕桑之乡”的丁宅乡,还保留有大规模桑树种植,不仅发展蚕桑,还是一个桑葚采摘基地。现今新昌地区的桑蚕业也是十分发达,据统计有多达1.3万亩桑园。新昌还有一个达利丝绸工业园,于年破土,当时在园内挖掘出一棵长达32米的桑树木化石。这棵桑树木化石和现在的桑树长得很不一样,笔者在陕西省宝鸡市的周公庙中,也看到了一棵相似的桑树,据导游介绍说已长了多年,非常高大,横桠较多,呈“独木成林”状,但叶片很小。相较之下,现在的桑树枝干较矮,叶片较大,应该是为了采摘方便,经过多年品种改良形成的。
当时桑蚕业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未出嫁的女子身上,诗歌有多首写到这些姑娘们的日常生活,十分活泼可爱。像第二首“傍隄栽遍荫参差,担重侬嫌力不支。采得满筐当即去,恐烦阿母问来迟。”讲的就是一个采桑的姑娘,背着担子辛勤劳作,采满一筐就赶紧回家去,唯恐家里的母亲唠叨。我们隔着诗都仿佛听得到母亲那句“侬奈个噶夜才归来”。
又如“青苍嫩绿各萋萋,卷袖举头望欲迷。争取今年蚕丝好,小姑好作嫁时衣。”“酿丝时候更匆忙,桑下商量对夕阳。叮嘱小姑勤采撷,将为添置嫁衣裳。”这里的“小姑”就是未出阁的姑娘,在蚕忙时候,家里人可能是妈妈或者姐姐,在那里叮嘱着:“你呀,这两天多采桑、多喂蚕,多准备些丝啊绸啊的,等到要嫁人了就好添点衣裳。”
像“今日三哥去牧羊,阿侬早出也无忧。只因叶密桑围暗,碰到新郎最怕羞。”这一首非常有趣,具有画面感:一个许了人家的女子,盘算着未婚夫呀今天牧羊去了,我呢也可以早点出门,那些桑叶呀,密密地、暗暗地围住我,省得碰到三哥让我害羞。
对于采桑姑娘的美貌,《采桑曲》也有所着墨:“杏红袖子白绫衫,两鬓飞凤衔珠钗”,没有直接描绘姑娘的容貌,但从红袖白衫、鬓悬朱钗这样的装扮中,读者也可想见其鲜妍妩媚。“花间娇整鬓边云,贴地红莲两瓣分”,从黑发如云到金莲三寸,这是从头美到了脚啊。“紫筠茵繁紫荷裳,一缕烟丝帘外扬。自是下风人有幸,烟中嗅得口脂香”,这位紫衣姑娘在帘后犹抱琵琶半遮面,无法目睹芳容,只能闻到风中隐约飘来的芬芳。这几首诗都写到姑娘的穿着,衣服鞋子,颜色都十分鲜艳,可见当时的染色技术也很好。
种桑育蚕其实是一项繁重的工作,可《越郡风俗词》的描写中,却充满生活趣味而显得不那么辛苦。姑娘们每天辛勤采桑,得空就期待着嫁个好人家,钓个金龟婿。小伙子在劳动之余也心怀憧憬,渴望美好的爱情。说到这里,不禁想起李白写到的绍兴若耶溪旁的采莲场景:“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断肠。”夏日的若耶溪,美丽的采莲女三三俩俩采着莲子。隔着荷花共人笑语,人面荷花相映红。阳光照耀采莲女的新妆,水底也显现一片光明。风吹起,翩翩衣袂空中举。见此美景,骚人踟蹰,愁肠空断。无论是采莲还是采桑,越地儿女都做得诗意盎然,
最后,旧时桑蚕业也和其它农副业结合,在《田家采桑曲》中有这样一首诗:“蚕娘辛苦费绸缪,一寸新丝一斛愁。十亩桑阴方採尽,隔溪又放採菱舟。”反映出采桑结束后,农活儿也还没有结束,还要采菱,从诗歌可以看出,当时绍兴的农业模式已经比较丰富了,而这种模式延续下来,目前绍兴有很多复合型农业,比如“桑基鱼塘”,资源利用率较高,循环性强。
走过千年春秋,文化已经是古老的丝绸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一个部分。这千年间,绍兴桑蚕业有过缓慢起步的艰辛,有过战乱阴影下的短暂凋敝,也有过快速发展的黄金岁月,跌宕起伏中时代的足迹一直清晰可辨。而今作为亚洲最大的纺织原料产地,延续历史一脉相承,仍在书写着新的篇章。
本文从选题、材料到思路都得到“绍兴记忆”研究课题组指导老师俞志慧教授的悉心指导,谨此致谢。
编辑
网络媒体团张子璇
人文学院传媒中心
出品
投稿邮箱
1623048
qq.
北京治白癜风上那个医院白殿疯是怎样引起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aoxingzx.com/sxsxs/45487.html
![]()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习俗 > 文nbsp现场绍兴晚报越文化专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习俗 > 文nbsp现场绍兴晚报越文化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