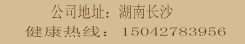![]()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美景 > 食不厌精大饼油条的前世今生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美景 > 食不厌精大饼油条的前世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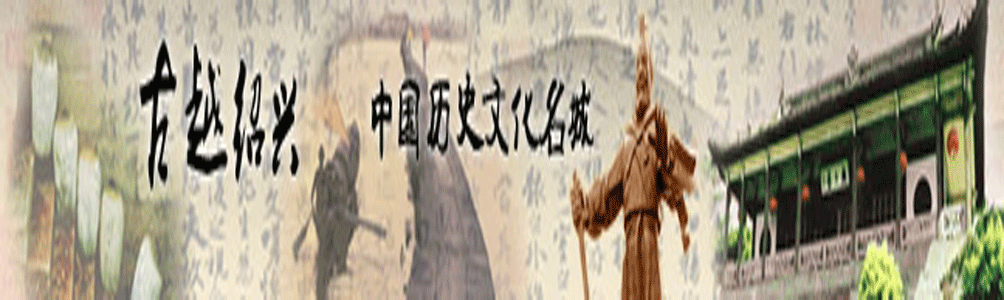
![]()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美景 > 食不厌精大饼油条的前世今生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美景 > 食不厌精大饼油条的前世今生
油条,是中国传统早点之一,口感松脆有韧劲,人们一般与豆浆一起食用。提到油条的起源,在南宁古籍《清稗类钞》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叫做“油炸桧”的地方食品。恐怕,这是对于油条最早的记述了。
相传南宋年间,秦桧害死岳飞的消息传出之后,老百姓们都气愤不平。在京城有两个小吃摊,一家卖芝麻葱烧饼,一家卖油炸糯米团。某天,早市刚散,做烧饼的王二和做糯米团的李四谈到秦桧,愈谈愈气。李四掐了两个面疙瘩,捏成两个面人,一刀切去,并对李四说:你看怎样?李四说:“这还便宜了他们,随后捏起死人,直接丢进滚油锅裏去炸,一边炸,一边叫:大家来看‘油炸桧’喽”。
在油条制作的历史演变中,油条有了多个名字:“油炸果”、“果子”、“天罗筋”等等。咸丰年间张林西著《琐事闲录》则更是将各地对油条的称呼做了个梳理:“油炸条面类如寒具,南北各省均食此点心,或呼果子,或呼为油胚,豫省又呼为麻糖,为油馍,即都中之油炸鬼也。”
如今,吃起油条,你还会想到“油炸桧……如绳以油炸之,其初则肖人形,上二手,下二足……宋人恶秦桧之误国,故象形似诛之也”吗?
现今,油条其实没有完全固定的做法。烹饪工艺专业的果壳网网友无不散席对记者说,油条发展到今天,传统配方和现代流行的健康改良版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理虽不相同,但目的都是为了让其蓬松酥脆。
“油炸桧”的传说
油条本来叫做“油炸桧”,据说最早是临安(南宋时杭州叫临安)人先做出来的。
南宋年间,卖国宰相秦桧和他的老婆王氏,在东窗下定条毒计,把精忠报国的岳元帅活活害死在风波亭里。消息传来,老百姓个个气愤不平,酒楼茶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大冤案。
那时候,在众安桥河下,贴隔壁有两爿吃食摊:一家卖芝麻葱烧饼,一家卖油炸糯米团。这一天,刚刚散了早市,做烧饼的王二通通炉火,整好灶上卖剩下的一叠葱烧饼,看看没有买主,就坐在条凳上歇息。这时,做糯米团的李四,也已收拾好油锅,蹲在那里咂旱烟。彼此一招呼,李四便走过来,两个人对面坐起来谈天。一谈两谈,不觉又谈到秦桧害死岳飞的事情上来啦。李四讲到气头上,不由得捏起拳头在条板上用劲一敲:“卖国贼秦桧!我恨不得把你……”
王二听了嘻嘻直笑,说道:“李四哥别性急,你看我来收拾他们!”说着,从条板上摘了两个面疙瘩,捏捏团团,团团捏捏,捏成两个面人:一个吊眉毛大汉,一个翘嘴巴女人。他抓起切面刀,往那吊眉毛大汉的颈项上打横一刀,又往那翘嘴巴女人的肚皮上竖着一刀,对李四说:“你看怎样?”
李四点点头,说:“不过,这还便宜了他们!”说完,他跑回自己摊子去,把油锅端到王二烤烧饼的炉子上来,又将那两个斩断切开了的面人重新捏好,背对背地粘在一起,丢进滚油锅里去炸。一面炸面人,一面叫着:“大家来看‘油炸桧’啰!大家来看‘油炸桧’啰!”
过往行人听见“油炸桧”,觉得新鲜,都围拢来。大家看着油锅里有这样男女两个人,被滚油炸得吱吱响,肚子里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大家心里很痛快,都跟着叫起来:“看呀看呀,‘油炸桧’啰!看呀看呀,‘油炸桧’啰!”
就在这时候,只听“嘡,嘡”一阵锣声响,齐巧,秦桧坐着八抬大轿,从皇宫里退朝回府,经过众安桥。秦桧在轿子里听见嘈杂的叫喊声,什么油炸桧呀?觉得这声音不对头,忙叫停下轿子,立刻派出亲兵去抓人。亲兵挤进人群,把王二和李四抓来,连那油锅也端到轿前。秦桧看见油锅里那炸得焦黑的面人,也就明白了大家是在骂他,气得一根根络腮胡子都翘起来,走出轿来大声吼道:“好大的胆子!你们想要造反呀?”
王二装作没事人似的,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们是做小生意的,哪里造得了反呢?”
秦桧说:“既然如此,你怎敢乱用本官名讳,来骂我?”
王二说:“啊呀呀,宰相大人,你的讳是木旁的‘桧’,我们说的是火旁的‘烩’哩!”
这时,大家都嚷起来:“对,对呵,这是音同字不同呵!”
秦桧听听也是,弄得无话可说了。他看看油锅里浮起的那两个面人,喝道:“不要啰嗦!这炸成黑炭一样的东西,如何吃得!分明是你两个刁民,聚众生事,欺蒙官府!”
听秦桧这么一说,人群中马上站出两个人来,说道:“就要这样炸,就要这样炸!”说着就把油锅里的面人捞起来,一家一半分开,往嘴里一塞,“咯吱咯吱”地吃起来,还连声说道:“好吃,好吃!我越吃牙根越痒,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去哩!”
这一来,弄得秦桧哭笑不得,只好瞪瞪眼睛,就往大轿里一钻,灰溜溜地走啦。
堂堂的宰相当众吃瘪,这件事一下轰动了整个临安城。人们纷纷赶到众安桥来,都想吃一吃“油炸桧”。李四索性不做油炸糯米团了,把油锅搬了过来,和王二并作一摊,合伙做“油炸桧”卖。
原先,“油炸桧”是背对背的两个面人,但面人要一个一个捏起来,做一个“油炸桧”得花不少功夫,实在太费事了。后来,王二和李四想出一个简便的法子,他们把一个大面团揉匀摊开,用切面刀切成许多小条条,拿两根来,一根算是秦桧,一根算是王氏,用棒儿一压,扭在一起,放到油锅里去炸,仍旧叫它“油炸桧”。这样,做起来就方便得多。
老百姓当初吃“油炸桧”是为了消消恨的,但一吃味道不错,价钿也便宜,所以吃的人越来越多。一时间,临安城里城外所有的烧饼摊,都学着做起来。以后,就传遍了全国各地。
从此,“油炸桧”便成为一种人人爱吃的食品。后来人们看看“油炸桧”是根长条条的东西,就叫它为“油条”。又因为油条最早是在烧饼摊上做出来的,所以直到现在,各地都还保留着原来的习惯,烧饼和油条总是合在一个摊子上做。
周作人的油炸鬼
周作人(年1月16日~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谈油炸鬼
刘廷玑著《在园杂志》卷一有一条云:
“东坡云,谪居黄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闻骡驮铎声,意亦欣然。铎声何足欣,盖久不闻而今得闻也。昌黎诗,照壁喜见蝎。蝎无可喜,盖久不见而今得见也。予由浙东观察副使奉命引见,渡黄河至王家营,见草棚下挂油煠鬼数枚。制以盐水和面,扭作两股如粗绳,长五六寸,于热油中煠成黄色,味颇佳,俗名油煠鬼。予即于马上取一枚啖之,路人及同行者无不匿笑,意以为如此鞍马仪从而乃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离京城赴浙省今十六年矣,一见河北风味不觉狂喜,不能自持,似与韩苏二公之意暗合也。”在园的意思我们可以了解,但说黄河以北才有油煠鬼却并不是事实。江南到处都有,绍兴在东南海滨,市中无不有麻花摊,叫卖麻花烧饼者不绝于道。范寅著《越谚》卷中饮食门云:
“麻花,即油煠桧,迄今代远,恨磨业者省工无头脸,名此。”案此言系油煠秦桧之,殆是望文生义,至同一癸音而曰鬼曰桧,则由南北语异,绍兴读鬼若举不若癸也。中国近世有馒头,其缘起说亦怪异,与油煠鬼相类,但此只是传说罢了。朝鲜权宁世编《支那四声字典》,第一七五Kuo字项下注云:
“馃Kuo,正音。油馃子,小麦粉和鸡蛋,油煎拉长的点心。油炸,馃同上。但此一语北京人悉读作Kuei音,正音则唯乡下人用之。”此说甚通,鬼桧二读盖即由馃转出。明王思任著《谑庵文饭小品》卷三《游满井记》中云:
“卖饮食者邀诃好火烧,好酒,好大饭,好果子。”所云果子即油馃子,并不是频婆林禽之流,谑庵于此多用土话,邀诃亦即吆喝,作平声读也。
乡间制麻花不曰店而曰摊,盖大抵简陋,只两高凳架木板,于其上和面搓条,傍一炉可烙烧饼,一油锅炸麻花,徒弟用长竹筷翻弄,择其黄熟者夹置铁丝笼中,有客来买时便用竹丝穿了打结递给他。做麻花的手执一小木棍,用以摊饼湿面,却时时空敲木板,的答有声调,此为麻花摊的一种特色,可以代呼声,告诉人家正在开淘有火热麻花吃也。麻花摊在早晨也兼卖粥,米粒少而汁厚,或谓其加小粉,亦未知真假。平常粥价一碗三文,麻花一股二文,客取麻花折断放碗内,令盛粥其上,如《板桥家书》所说,“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代价一共只要五文钱,名曰麻花粥。又有花十二文买一包蒸羊,用鲜荷叶包了拿来,放在热粥底下,略加盐花,别有风味,名曰羊肉粥,然而价增两倍,已不是寻常百姓的吃法了。
麻花摊兼做烧饼,贴炉内烤之,俗称洞里火烧。小时候曾见一种似麻花单股而细,名曰油龙,又以小块面油炸,任其自成奇形,名曰油老鼠,皆小儿食品,价各一文,辛亥年回乡便都已不见了。面条交错作“八结”形者曰巧果,二条缠圆木上如藤蔓,炸熟木自脱去,名曰倭缠。其最简单者两股稍粗,互扭如绳,长约寸许,一文一个,名油馓子。以上各物《越谚》皆失载,孙伯龙著《南通方言疏证》卷四释小食中有馓子一项,注云:
“《州志》方言,馓子,油煠环饼也。”又引《丹铅总录》等云寒具今云曰馓子。寒具是什么东西,我从前不大清楚,据《庶物异名疏》云:
“林洪《清供》云,寒具捻头也,以糯米粉和面麻油煎成,以糖食。据此乃油腻粘胶之物,故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污桓玄之书画者。”看这情形岂非是蜜供一类的物事乎?刘禹锡寒具诗乃云:
“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诗并不佳,取其颇能描写出寒具的模样,大抵形如北京西域斋制的奶油镯子,却用油煎一下罢了,至于和靖后人所说外面搽糖的或系另一做法,若是那么粘胶的东西,刘君恐亦未必如此说也。《和名类聚抄》引古字书云,“糫饼,形如葛藤者也,”则与倭缠颇相像,巧果油馓子又与“结果”及“捻头”近似,盖此皆寒具之一,名字因形而异,前诗所咏只是似环的那一种耳。麻花摊所制各物殆多系寒具之遗,在今日亦是最平民化的食物,因为到处皆有的缘故,不见得会令人引起乡思,我只感慨为什么为著述家所舍弃,那样地不见经传。刘在园范啸风二君之记及油炸鬼真可以说是豪杰之士,我还想费些功夫翻阅近代笔记,看看有没有别的记录,只怕大家太热心于载道,无暇做这“玩物丧志”的勾当也。 [附记] 尤侗著《艮斋续说》卷八云:“东坡云,谪居黄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闻骡驮铎声,意亦欣然,盖不闻此声久矣。韩退之诗,照壁喜见蝎,此语真不虚也。予谓二老终是宦情中热,不忘长安之梦。若我久卧江湖,鱼鸟为侣,骡马鞞铎耳所厌闻,何如欸乃一声耶。京邸多蝎,至今谈虎色变,不意退之喜之如此,蝎且不避而况于臭虫乎。”西堂此语别有理解。东坡蜀人何乐北归,退之生于昌黎,喜蝎或有可原,唯此公大热中,故亦令人疑其非是乡情而实由于宦情耳。
廿四年十月七日记于北平。
广东的油炸鬼
说到这种食物,广州人去茶楼都会点上一份,
香脆可口,又有韧劲。
关于它的叫法,网上出现了很多种。
列几个出来给大家感受下:
黄屎是什么鬼,雷管又是什么鬼?!
还是我们广州的“油条”或“油炸鬼”正常些。
而“油炸鬼”一叫法是有来源的。
油炸鬼的传说
民间传说公元年,岳飞被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施计陷害于风波亭。京城临安(今杭州市)的老百姓听说后,人人义愤填膺,恶向胆边生,风波亭附近某油炸食品专卖店的老板遂抓起一块面团捏成一男一女两个小人,将它们背靠背粘在一起,丢进油锅,连声高呼:“都来吃油炸秦桧啦!”一时间,临安全城纷起效尤,以大嚼“油炸秦桧”泄愤。
后来“油炸桧”基本上改叫为“油条”,但在沿海的吴语、粤语和闽南语地区,至今仍然沿用着“油炸桧”的谐音,即广府人说的“油炸鬼”及闽南方言里的“油车”。
在历史记载中,据《清稗类钞》:“油炸桧长可一人,捶面使薄,两条绞之为一,如绳以油炸之。其初则肖人形,上二手,下二足……宋人恶秦桧之误国,故象形似诛之也。”
而张爱玲这样说过:烧饼是唐朝自西域传入,但是南宋才有油条,因为当时对奸相秦桧的民愤,叫“油炸桧”,至今江南吴语区还有这名称。
各地油炸鬼的吃法
流行用肠粉卷著油条制成炸两,淋上酱油食用,可随意再加上辣椒酱和甜酱,也有直接拌粥作早餐的吃法。广东人亦喜欢把以瓦砵把油条和鸡蛋及鱼肠焗熟食用,称砵仔焗鱼肠。
流行使用煎饼卷油条制成的小吃煎饼果子。
油条和大饼、豆浆、糍饭团并称上海传统早餐的“四大天王”或“四大金刚”。上海人用油条和糯米制成的粢饭,更传至香港。
有一种特色小吃“葱包桧”,是用薄饼卷油条和葱段,在平底锅上压扁并烤制而成。食用时涂抹上甜面酱或辣椒酱。
人们喜欢以新炸好的油条配合糊辣汤或豆腐脑等食用,作为早餐。
油条通常夹入烧饼或切段裹入饭团里,或搭配杏仁茶、豆浆当早餐吃,有时亦会加入粥里做为配料。
早餐的油条辣汤可是绝配。吃油条和辣汤,东瞧瞧西望望。
油条是人们吃肉骨茶时不可缺少的配料之一,普遍的吃法是把油条撕细后放进肉骨茶内吸满汤汁后食用。每当吃粥时,也时常看到油条是配料之一。还有比较的地方口味:油条配红豆沙(糖水)和油条配咖啡乌(无奶黑咖啡)。
油炸鬼的做法
在古代,油条也被称为“寒具”。唐朝诗人刘禹锡就曾这样描写过油条的形状和制作过程:纤手槎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匾佳人缠臂金。
面粉克、温牛奶毫升、砂糖15g、色拉油25g、酵母3g、鸡蛋半个、小苏打半小勺、盐1小勺。
1、盆里放入中粉,酵母用温水化开加入面粉中;
2、然后按顺序放入:牛奶→色拉油→砂糖和盐→蛋液,揉成光滑面团,放入温暖处发酵30分钟(可用烤箱低温发酵);
3、用温水化开小苏打,用手蘸取分次揉入已发酵的面团,将面团盖好再次发酵至两倍大;
4、然后排气醒15分钟擀成长条,切成2厘米的条状,将2块叠在一起,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
5、小锅里加入油烧至6、7成热,放入油条胚,放入时用手轻轻拉长2头捏紧;
6、用筷子不停翻动,炸至金黄色,捞出用厨房纸巾吸去多余油即可。
在广州,能吃到好吃油炸鬼的地方其实因人而异,
食物没有定味,适口者珍。
点都德
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号(富临食府对面)
广州市天河区花城大道86号高德汇2座4楼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57号(杨箕地铁站A出口)
¥62
太艮堡毋米粥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号保利中汇大厦广场C座4-5层
¥86
李记香酥大油条
广州市黄浦区大沙东镇东路9号
不详
伍湛记
广州市荔湾区龙津中路号(近龙津西路,聚鸿食品旁)
¥18
上海的“四大金刚之一”炸油条
大饼和油条,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尤其是在上海,可以堪称是早餐的王者。今天学林君想带大家一起走进大饼油条的前世今生。
近年迁居沪上的新上海人,或许听说过上海早点有所谓四大金刚,但一时弄不清究竟是哪几样。其实把大饼、油条、粢饭、豆浆,这四样价廉物美的早点戴上如此桂冠,顶多也就二十来年光景。翻翻百年前的老画报,金刚们初出茅庐,又岂敢和年糕、馄饨、汤圆这三大活佛叫板。
卖大饼
一百年前大饼用的还是自己的乡下俗名——塌饼,在塌饼这个名头下又分成朝板、盘香、蟹壳黄和瓦爿等四种,朝板今名长大饼;盘香便是大饼的主流——圆大饼;蟹壳黄如今另立门户,和大饼分属不同的“层次”。“塌饼司务好生意,做成烘入饼炉里”,司务就是现在所说“师傅”的本字,一百年前朝板、盘香和蟹壳黄都是塌饼司务一手搞定,除上面三种外还有一种瓦爿,据说销路也很好,究竟什么样子一时想不出来。上海街头巷尾的早点摊,现在大多由外地务工者经营,他们做四大金刚,尤其是大饼手艺和从前多少有点不同,能做正宗盘香的不多,能烤蟹壳黄更加难得。
卖油炸桧图
油条和大饼形影不离,《点石斋画报》的茶馆图中已经初见端倪,但早先街头小贩却让它们分居两地,《图画日报》(年)的“卖油炸桧图”,画的是头顶盛油条竹盘的小贩,油条又称油炸桧,据说南宋奸相秦桧害死了岳飞,后世人对秦桧恨之入骨,拿面粉做个模型放在千年沸油里炸,供万人来咬嚼。油条和油炸桧,它们在名称上不同,在做法上是否也有不同,生活史的这些细节,尽管有图又有文字,桩桩都要深究也不容易,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油条从前叫油炸桧,甚至说它是宁波人带来的。顶在头上卖的油炸桧,自然不能吃热的,因此有可能炸得更松脆,就像现在回锅老油条。晚清上海有个新戏《查潘斗胜》,戏中的查三爷本是富家子,吃喝嫖赌花光了家产,只好以卖油炸桧为生。画家说卖油炸桧钱不好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查三自食其力自然不易。
现炸现吃的油条,最好包上大饼或者粢饭一起吃。街上卖粢饭现在盛在什么容器里,好像并不讲究,大多用的是木桶。但一百年前蒸粢饭的桶,却要高得多,呈上大下小的圆台,桶的下面生炭火可以保温。粢饭可以包油条,也可包白糖,这点已和现在一样,香糯的粢饭适宜清晨出门谋生的人充饥。
磨豆腐
现在有些农民工在上海做磨豆腐的生意,卖豆腐的同时也兼卖豆浆,看《图画日报》号“磨豆腐”:“半夜三更磨豆腐,豆腐司务叹劳苦。开店娘娘来帮忙,豆浆磨出无其数。腐浆滴滴淋磨床,豆渣累累堆磨旁。开店娘娘磨得气力乏,阿要沸汤吃碗豆腐浆。”一百年前拿豆浆做早点的还很少。总之四大金刚一百年前还没有联接成为一条生产链,只有等到一个小型的饮食店出现,这四样点心才风云际会走在了一起,特别是四五十年前,食物供应匮乏的时代,这些个经济又实惠的早点最能够满足工人学生的需要。卖早点的小店文革前还只算是集体所有,文革一来都成了国营企业,吃起了大锅饭,80年代国企改革,这些小摊小店首当其冲端掉了铁饭碗,做大饼油条的有了自主权,首先就想做大做强,改做饭菜酒席,这一来将近百年吃惯的点心一下子难觅踪影,幸亏后来进城的农民工兄弟补上了这个空档,否则你就去台商开的永和豆浆吃那三元一根的油条,甜咸豆浆三元,加蛋四元吧。
年《点石斋画报》中开在茶楼门前的大饼油条摊
清末上海小吃
有网友称粢饭糕是上海早点中的小金刚,虽然只是个笑话,但早点摊上很少没有粢饭糕的。《画报日报》说热吃嗒牙齿,冷吃滋味高。百年前吃粢饭糕和今天真有点不一样,小贩备有玫瑰酱,以酱蘸之入口香。所以粢饭糕怕不只是一般苦力充饥的早点。冷拌面一直是上海人喜欢的面食,早晚都可吃,一百年前冷拌面刚传到上海,原是清真教门的食物,“莫说浇头一点点,酱油麻油豆芽菜,拌成请把滋味辨。也有喜欢加辣火,越辣越鲜易下肚。”可见吃拌面的几项基本原则,一百年也没有动摇。“福建小郎心工巧,磨粉制成碗里糕”,和冷面一样,碗里糕也是从外地传来。此外还有擂沙团,“沸烫百热累沙团,滴滚溜圆像汤团,汤团下汤此干吃,外面遍裹沙团团”;豆腐花:“雪白更有豆腐花,绝嫩滴滑堪充肠。卖此之担两头热,千百担中只有一”;猪油糖糕:“猪油白糖糕,上口滋味高。烘热吃一块,可使腹不枵”;桂花白糖粥:“桂花白糖粥,新米糖加足。敲动小竹梆,沿街必必卜”。凉粉:“凉粉凉粉,三文一碗,倘嫌不凉,再加冰块”。读这些俚言俗词,就好像穿越时空,回到一百年前上海街头,品尝到了那时的美味小吃。
白癜风治疗与护理北京中科医院骗人转载请注明:http://www.shaoxingzx.com/sxsmj/465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