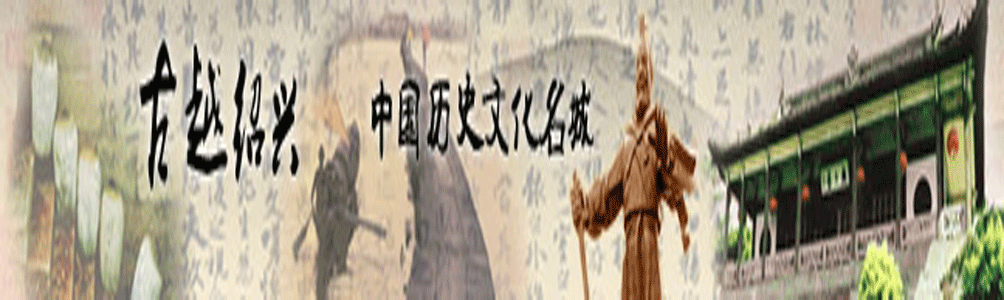绍兴则水牌,即将消逝的老渔村
人类学家说,江河合流的地方最适合人类生存。
则水牌,是一个古老的注脚。这个存续了多年的渔村,早在春秋时期,则水牌(时称为巫山里)先民已在湖湾江汊中生息,代代繁衍。
多年过去了,承载着渔业、造船业、水上运输业等发展史的则水牌,随着城市的足迹踏到家门口,工业化的喧嚷,已经苍老不堪,终将成为历史的记忆。
走进老渔村
则水牌,一个古村,却有着与多年古城同样的岁数。
早在春秋时期,则水牌(时称为巫山里)先民已在湖湾江汊中生息,代代繁衍。
多年过去了,承载着渔业、造船业、水上运输业等发展史的则水牌,随着城市的足迹踏到家门口,工业化的喧嚷,已经苍老不堪,终将成为历史的记忆。
站在则水牌村口,抬眼就是绍兴客运中心的繁忙无比,迪荡新城的现代繁华以及川流不息的车来人往。她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都市里的乡村”。回望村子,棚户连片,茅厕遍地,破乱不堪……
这似乎就是她的最后写照。
因此,拆迁,成了她最后的归宿。
5月末,则水牌村民收到一张红纸,那是东湖镇政府写给他们的一封信,“政府将适时推进该区域的拆迁……而六七两个月将对拆迁房屋进行丈量调查……”
当这一官方消息公布时,则水牌瞬间沸腾了。
初夏的一个上午,记者沿着则水牌最宽阔的马路——会龙大道从南向北走去,惊讶于此地人气之旺,仿佛在办庙会,热闹得有点凌乱,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开着汽车叫卖水果,着地摆摊卖衣物,当然更有则水牌地方特色的卖渔网店铺。
当地人一脸自豪地说,则水牌一直被称为“小上海”,原住民1.2万人,外来人口2万人,人口稠密,经济繁荣。
在则水牌的街头稍一停驻,记者听到一阵议论,“你家房子有没有来丈量过?面积多少?”如果你多打量一下这条老街,询问一下古村的历史,当地的居民立即凑拢过来询问,是否与拆迁有关?
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序曲。
记者从会龙大道向左拐入,发现则水牌四面环水,时光在这里是停滞、徘徊,缓慢地行走。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则水牌人除了翻建自家的老屋外,变化不大。古老的石板路,狭长的小巷,仅容一人而过,有伸出很长的屋檐的老房子,小河从家门口流过,河里充斥着各种生活垃圾。
不过,最近十来天,这个村子在大兴土木,不少人家把屋檐改成房间,二三楼的阳台变房间……新砌的红砖还来不及上水泥,非常醒目。
据了解,则水牌区域的拆迁,已经传了许多年,当地人好几回伸长脖子期盼。但当多年的传闻变为现实,许多人倒生出几许怀疑。
一位只剩几颗当门残牙、头发稀疏的老太,坐在自家的两间平屋里。记者与她聊,她说自己18岁嫁到这里,已经在此住了60多年,生有4个儿女。
“都在说房子要拆了,我不识字,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她的老头提醒她,村里已经下发了红纸头。不过真要拆迁,估计也要好几年,我们都八十好几了,不知能否盼到这一天。
65岁的渔民高阿狗,祖祖辈辈住在则水牌。此刻,他坐在水产村办公室里,说起则水牌拆迁,他流露出一丝不屑,“拆迁后住高楼,谁稀罕?我家的房前有一条河,有一块开阔的道地,夏天,可晒几十匾虾干,冬天,可晒几百条鱼干,拆迁后,晾晒何处去。当然,为了子孙后代考虑,拆迁就拆迁吧,下一辈人的确住不惯老屋了。”他说。
古代测量水位之地
“则水牌,在越王勾践时期,称为巫山里,南宋绍兴年间,巫山里改名为则水牌,清乾隆年间改为则水乡,清宣统时代改为会龙。”年出版的《则水牌志》载。
今天,关于则水牌的称谓,当地人一会儿称则水牌,一会叫会龙。公交站牌上,又写着侧水牌,地名之繁杂,令外人一时混淆不清。
正如村名称谓一样,当地人说则水牌的历史,版本也不止一个。
民国《绍兴县志资料》载:则水牌,在第一区会龙乡,县北昌安门外十五里,初名巫山乡……戴琥竖则水牌于此,遂称今名。
在当地人看来,则水牌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丢失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三块水则碑——“季水碑”“测水碑”和“金木水火土碑”,至今痛惜不已。
“季水碑”的竖立者是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他在巫山里立下“水则碑”(一名“季水碑”),根据季节和农时来控制水位的标尺。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绍兴知府戴琥为了规范绍兴内河河网水位的调度和管理,他设立了衡量水位、控制泄水量的标尺“测水碑”,位置就在则水牌的“季水碑”处。
到了明嘉靖十五年(),汤绍恩修建了三江闸,竣工后原“测水碑”处,重设了一块水则碑——“金木水火土碑”。
说起水则碑的位置,当地人钱志康站在船上,手指跨龙桥正南方与街河的交汇处说,测水碑就在此处。
当地百姓称,年,绍兴遭遇百年未遇之旱灾,跨龙桥下的河床全部露底。当时,有不少人亲眼目睹过一块石碑,长约2米,宽约1米,厚约15厘米,中间印着“金木水火土”五个字,倒在河床里……这块“水则碑”就是控制三江闸门启闭标准的水位标尺——凡水至金字脚,三江闸28个洞全部打开;至木字脚,开16个洞;至水字脚,开8洞;夏至火字头筑;冬至土字头尽筑。水位调度须恪守此规则。
只不过,这3块水则碑,如今只剩下回忆。
则水牌,这个古代测量水位的地方,倒是因为鉴湖、浙东运河的流经,而撑起了她几千年的富庶。
据载,在南宋,依水而存的则水牌村,因盛产鱼虾、稻米等,为闻名越州的大村落。这里沿河建街,集市小有规模,为越州境内富裕之村。
清代,乾隆十六年(),乾隆下江南,在会稽祭祀大禹后,一路巡游,途经则水牌。当他听说这里的人民为治理一方水利建有功勋时,龙心大悦,特为则水牌题书村名,并下圣旨鼓励则水牌百姓“善贾者经商,会手艺者做工,会耕作者种田,会落江者捕捞”。
乾隆期间,则水牌更是驰誉一方,沿街20余家店铺,一应俱全。手工业尤其是造船、织网、水产养殖等行业,名闻江浙。
今天的则水牌区域,包含则水牌、水产、松陵3个行政村和则水牌、新华2个居委会,依然以老祖宗留下的捕捞业为生,只不过发扬光大了,它建立了绍兴最大的大昌水产批发市场,绍兴市民所吃的水产品80%来自于此。
渔民的明天
人类学家说,江河合流的地方最适合人类生存。
汩汩的鉴湖和浙东运河是则水牌的生命之源,它世代给村子带来鱼虾蟹鳗等,带来财富和机会,成为远近闻名的渔村,应运而生一大批渔民。
渔民钱志康,今年56岁,身高1.82米,体重近公斤,他的一双手,黝黑红肿,指缝间长着白色的湿气,那是捕鱼的印记。
他9岁跟着父亲落江(即捕捞作业),年龄稍长,辗转于绍兴的一些水库里抲鱼,从25米高的大打网,到中打网、小打网,他都干过。
“则水牌渔民捕捞的作业不下10种,照虾、摸虾、滚钓、拖别、打滥等等,捕鱼方法不一。”他说。
打渔是辛苦的。他半夜12点起床,划着小船落江,一大早拿到市场里卖,晚上八九点钟躺下,再半夜起床落江,周而复始。
今天的钱志康,不当渔民改行水产养殖,在瓦窑头承包了60亩水面,养鱼养虾,他的妻子在白马畈农贸市场卖水产,夫妇分工合作,小日子过得幸福美满。他的家位于会龙大道,一幢小洋楼,崭新的喜字还贴在门上,儿子小钱刚刚结婚成家,不过小钱无意于继承父业,他改行搞废旧金属回收。
渔民高阿狗,7岁落江钓鳗,15岁打网捕鱼。年轻时,他半夜起来,划着小船外出钓鳗,伏在一个洞口用虾诱鳗出来,有时一个洞就能够钓到十来条鳗。
“一条野生鳗长到1斤重,需要七八年时间,养殖鳗只需一年,速成。但是,口味不一样了。那时候的鳗蒸出来,油珠是黄色的,肉是结实的,那个鲜!”高阿狗边说边摇头,野生的鱼虾鳗蟹几近绝迹。
与之一并绝迹的,是渐渐老去的渔民。
则水牌四面环水,该村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先前都是落江“找钱”——捕捞水产品、贩销水产品、外拓承包水面,等等。
只是当则水牌拆迁后,渔村终将消逝,渔民将何去何从?
这似乎是一个未知数,但却是一种必然。
它的消失,如同那些延绵千年而不再的老手艺。
在则水牌,一位84岁须发皆白的老汉,坐在跨龙桥上聊起则水牌拆迁。他说,消失的不仅仅是村子、老屋,更早消失的还有老行当——凿缸砂、马桶砂。
记者不知此为何物?他说,那是一个古老而今匪夷所思的行当。传统农村的马桶和茅厕的壁和底上,年久结砂,则水牌有人曾操此业,手拿錾子和锤子,把这层砂凿下来。
这层砂经过暴晒,再用臼石搡碎成粉末,入中药成一味,也是农作物和苗木果树的上乘肥料,堪称珍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农村改厕,渐弃马桶,肮脏、辛苦又危险的凿缸砂、马桶砂行当,也就销声匿迹了。
只是,当古村消失后,何处是乡愁?
大概只有在则水牌人的梦里,以及谈资中了。(记者沈卫莉沈伟文何雯沈伟 摄)
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最好北京哪有治白癜风的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aoxingzx.com/sxsly/43080.html
![]()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旅游 > 绍兴则水牌,即将消逝的老渔村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旅游 > 绍兴则水牌,即将消逝的老渔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