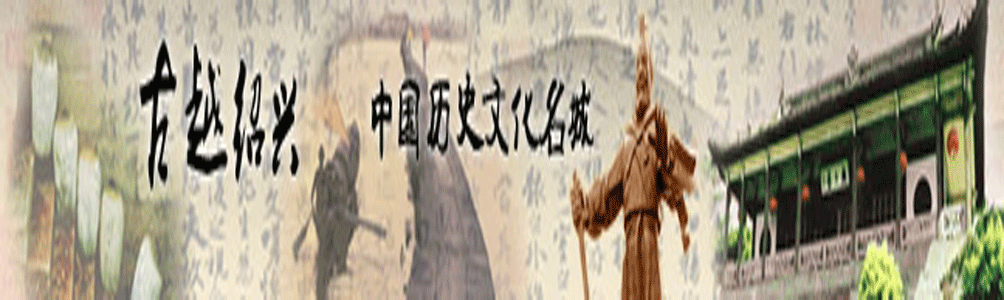绍兴不光有黄酒文化,一名老者讲述解放初的
不到十岁的时候,我就是个小戏迷。当时能在乡下唱的也就是绍兴大班和越剧。越剧当时村人称之为“的笃班”,我最初看到的“的笃班”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章家祠堂的两棵大梧桐树下搭的戏台。剧中那委宛的唱腔,抒怀的音乐令我听得如痴如醉。
我们乡下,演戏大多在庙里,庙殿正堂供奉的菩萨各有不同,如果在关帝庙,那就是关帝菩萨。殿前有个小广场,前面坐南朝北的门楼可以做戏台,一人多高,唱戏时漏空的木板上会铺块地毯,台后简易板房便是演员上妆休息处,演出时观众从边门进出。庙宇都是有围墙的,鲁迅先生所描写的:台上群玉班,台下都走散;.....连忙关庙门,墙头都爬翻。的情况,我还没碰到过,想看戏得凭票,那时的票价也就是5分钱。固然是由于正式的戏班人数不多,“跑龙套”之流都有本乡人业务担当,我们家的邻居“3爹”便是演龙套的。“跑龙套”们一身戏装,扛着五色旗上场,只要随着喊几声“呵—”四个人在台四角这么1站,便可以站到剧目做完为止。我猜龙套们也没有劳务费,最多吃餐便饭,所以戏班的开支很省,乡下人历来不干烧钱的事!
但是这5分钱对我却是个大开消,从何而来?家境自己还是明白的,而这戏又非看不可。我想了个不花钱的好办法:关帝庙虽然已是个临时剧院,但下午五点前村民还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因而我选在五点前进庙,趁人不备偷偷钻进关老爷菩萨后面,1躲几小时。—我确信,事出无奈,祖母又带我在菩萨前寄过名,佛名“关根”,所以关帝菩萨决不会怪罪我。就这样偷偷地看着大关庙门清场,村民观众陆续进来,等庙里渐渐热烈起来的时候我悄悄从菩萨后面钻出混入人群,屡试不爽。
因而我挤过馄饨担,绕过油炸玉鳝丁鱼的小摊,瞧一瞧焞得焦黄的臭豆腐,咽咽口水,专心看戏台上开场的戏。“跑龙套”的“3爹”们出来了,喊着“呵—”;接着背上插着四支翠旗与头上帽顶插雉鸡毛的大将对打;看长须大官“咿咿呀呀”地唱。虽然没太看懂,但里面的热烈和有趣另我至今回味无穷。1直到大戏散场,我在黝黑中夹在兴奋的人群中回家,心里只想到吃饭,祖母和母亲一定还在家里等着。
那时候的我太小,根本记不清绍兴大班里的唱腔。直至后来看了“孙悟空3打白骨精”才会唱几句唐僧的“弟子东土唐三藏.....”和猪八戒的“断命猴头玩弄我......”这么简单的几句。但到了上绍兴1中的时候,我惊讶当时高年级的同学竟把鲁迅著作里写的“女吊”、“无常”等戏演得非常象样。“无常”伯伯的台词“不管那皇亲国戚,不管那兄弟妻侄......”竟和半个世纪前鲁迅笔下的如出一辙,那种草根气非常得浓重。我疑心老师导演中有高人在,一定是先生的铁杆粉丝,其实我们几个同学未尝不是鲁迅先生的铁杆粉丝?当时还编过话剧演“爱姑”,台词里那“杀头的赖皮狗,拱开了鸡橱门!”完全是原著里的。直至两年前L君请我看绍兴大班折子戏,也有“无常”和“女吊”,但许多词改得文人化,难道是为了“思想意识”或“主旋律”什么的?固然也好,但总有些“淡笋放汤”的味道。
看绍兴大班这几十年来仅是“偶尔一次”,其实说起来也够惭愧的,我已有二十多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一般的电影已看不到,乡镇一级已没有电影院了;大片又太贵,离看不起不远了。
年纪大了,现在看戏看电影总觉得没有之前好看,还是心情不一样了,兴趣不一样的关系吧。
中科UM-D北京中科医院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aoxingzx.com/sxshj/4213.html
![]()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环境 > 绍兴不光有黄酒文化,一名老者讲述解放初的
当前位置: 绍兴市 > 绍兴市环境 > 绍兴不光有黄酒文化,一名老者讲述解放初的